
最近,阿木有些火。人们不仅在谈他的“理想国”,还在谈他的“瓯江书院”。
被卢志文称道的翔宇牛人很多,但“阿木”肯定算是最先提及中的那一个,卢志文总是在他人面前夸奖他,说此人年纪不大,但书读得多,并放心地将翔宇“瓯江书院”(未来的图书馆)的筹建工作交给他……
在翔宇校园内,时常看到一个人,手捧一本书,行走在绿荫小道上,他就是“书虫”——阿木,真名叫叶玉林,生于1976年,来自四川泸州。许多人都知道他不但是翔宇高中部的一名受学生爱戴的语文教师,还是翔宇民间读书会的发起人,每逢周五晚上翔宇教师发展中心教师读书沙龙由他主持。有许多很铁的粉丝追随他的足迹,然而他的故事远不止这些。
他,在寻找,完成编写“思享者”读本,办小报14期,整理学生原创作品25万字;又开启了一系列梦想:规划读书沙龙,筹建书院,未来还想办一所学堂……
阿木这样描绘着未来“瓯江书院”的雏形:绿树环绕处有一幢青砖白墙的建筑坐落在学校的南大门河道处,期间有一个读书长廊,旁边有一泓池水,荷花簇拥中不时飘来一阵清香,许多学生模样的人群徜徉期间,或坐,或立,手捧书卷,静静地阅读……

因为新教育,因为“河边茶”,结缘翔宇
一开始不知道翔宇这个学校,但一直都比较关注“新教育”。像朱永新、卢志文、李玉龙等名字比较熟悉,特别是很多语文老师如蔡朝阳、郭初阳,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通过网络阅读,发现大家志趣相近。教书期间,认识了一批喝“河边茶”的人:张羽、龙尧、谭海舟,经常一起聊天,因为四川人比较喜欢喝茶,只要有一条小河、有一本书、有一棵树,就有一个茶铺,于是聊天群就叫“河边茶”了。后来这圈人基本上都到了翔宇。
一脚踏入他人的生活从而也走在自己的生活之路上
“一脚踏入他人的生活从而也走在自己的生活之路上,生活啊,活不够啊。” 阅读,让阿木有了的感慨。
读书要进入一种文化环境。高中时,略懂古文祖父给他买过好几本书,有《古文观止》、《红楼梦》、《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中国古代名句辞典》等。高中开始有一点阅读意识,读的第一本小说是《三国演义》,后来读了一点《史记》。最初是多读,后来是精读,反复读,多读几本译本。读书要读到相当的深度才能把其中的内涵说清楚。
两年前,他估算了一下近几年的阅读,每年阅读的书大约为40本,以每本25万字计算,约为一千万字,加上常常阅读“爱思想”一类的网站和《随笔》、《读书》、《书屋》等偏重学术性的文章和其他一些阅读,阅读量应当不会超过1500万字。而这些阅读大约有70%是通过电子书完成的,特别是前些年买了一个Kindle,看了一下上面的统计,读书时间为290天,总阅读时间605小时,平均每天2.1小时,读完的书籍为27本,主要阅读时间集中在下午3-5点。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阅读习惯:精读的书籍一般用纸质书,泛读用电子书,看网站上的文章用手机。
大学期间,外国文学类的书读得多。但是那时候读得很不专业,相对于走进大学就好像走进一个殿堂,那里有很多书啊。开始比较喜欢文学类的,先是法国的,雨果、巴尔扎克等,后是俄国的,更喜欢俄罗斯的文学,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他最喜欢的作家的果戈里。感觉法国人的文学,它大量交代一个宏大的历史,后来把一个小人物放到里面,历史把他碾碎,碾碎了然后呈现某种悲剧感,好像外来的力量施加给他。像法国文学里的《红与黑》、《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都有些类似的。但俄国的作品给人感觉更深沉一点。人类陷入自身的命运,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罪与罚》里面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他自己偷了人家东西然后把老太太杀死了,他一生都在这个里面纠缠。还有像《复活》里面的聂赫留朵夫。后来读到某个时候,发现俄国文学更能谈个人,更能回到人的内心,讲救赎啊,不像法国文学那种我的命运是时代造就的,而是我自己造就的。感觉有这个区别,只是不能一概而论。
工作以后在乡村中学教书,前面几年比较沉寂,没有那么强烈的阅读愿望,只想先忙好工作。世界尽管很糟糕,但世界的美好向正展开啊。但过了几年就发现教书的无力。于是埋头读书,2003年——2013年那十年属于他人生阅读从量来说最多、从质量来讲也很好的时期,不过,现在他醉心于精读东西方经典文本,《理想国》、《庄子》、《圣经》、《精神现象学》等等,并准备把这些变成一个“东西方经典文本细读”的系列课程。
在艰难的几年中,读海子的诗是一种安慰,这有点像古时的书生,落魄时就读读屈原,然后觉得生活还可以过下去。一个人的焦灼本质上意味着对人生的怀疑,他总会不断地寻找出口并付诸行动。

语文教学阅读本位——把学生当人看,编读本,办小报,刊原创
朱永新有一句话: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阿木认为这话说得很到位,现在许多人遇到事情没办法坚持,就是精神不够强大,没有人生目标,包括学生考大学,不知道自己的目标,绝大数学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就是缺乏精神发育啊,就像一颗种子,长大的时候,它刚刚开始它只是想从土地长出来,但长出之后它就知道向着阳光生长,思路与成长轨迹很清晰——学生缺乏的就是这个。而现在中国的教育没办法让学生寻找自己的方向,而是给学生一个方向,就是高考,以为这就是方向。而精神发育史,是无法替代的,它必须亲自去找。比如说一个老师这样教这样活,那个老师那样教那样活,这只是学生提供了一些参照,但学生不必按些生活。人不是按必然性生活的,康德的哲学所讲,一个叫自然,一个叫自由,自然就是一种必然性,这个力推过去那边一定反作用,但是人不同,你这样推过去的时候,他的可能有很多种。人的根本属性是自由,而这种自由,需要自己去生长,而不是被外界规定的,你规定就是不自由了。
你不能把学生只是当成一个工具,一种手段。“我真的不认为老师们有那么关心学生,一个老师真的关心学生他的做法完全不一样的。不能因为这个学生好了,他就高兴,学生不好了,他就不高兴。我觉得这就不算是真正关心。所以说中国教育缺什么,非得要说的话就是自由。说具体点的话,就是没有把学生当人看,包括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人看。不能是一个零件推动另一个零件。康德说当你不把别人当人看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没把自己当人看,就没有把人当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具有丰富的无限可能的生命体来看。我教书受康德的影响比较大。他的这些话确实有些道理,要把学生当人来教。”
阅读教学,他可能是老师中做得非常彻底的一个。他采取很多办法,编了《思享者》读本,有片段性的读本,目前编了180页左右,偏重于泛读;还有专题读本,像《世说新语》,偏重于精读。目前,他已在准备《理想国》读本——倾向于给学生一些经典,但同时容忍学生看一些他认为不经典的。他还一直坚持给学生办小报,刊登学生的原创作品,班级学生人手一张,到翔宇一年多,已经完成14期,每张报纸相当于一张A3张那么大,可容8000字左右。整理学生原创作品25字,计划编辑成一本文集发给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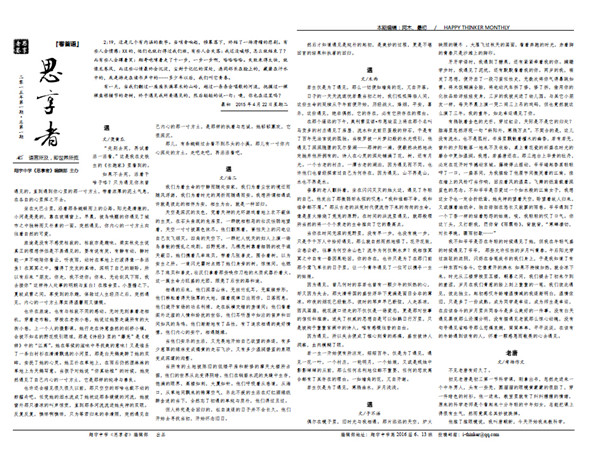
教育是一种信仰:第一个充分地阅读,第二个是生命的体验
阅读增加了,那么如何完成单元课时教学呢?阅读推进太多了,要牺牲一点,你教的班级成绩暂时没那么好,但他的想法是你想要踢足球只能在足球场踢不能在乒乓球台上踢,那样踢不转的。我认为“把人当人看”的教育观念跟中国当下的教育肯定是有尖锐冲突的,你躲不了的。教师个人要有充分的谋划,还要甘心承担一点代价。
必须要直面问题,第一个要深入研究中国的考试,我们这里是浙江的考试了,包括它的学考和高考。研究好了做出策略,比如有些文本,可上可不上的就不上了,有些文章要上但是它考得很少,那就把这个问题挑出来,把答案公布一下就可以了。“我追求我的自由,但不伤害别人的自由”,你看马丁·路德·金、甘地、曼德拉,他们其实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但恰好是他们帮助成就了一个更为自由的国家,自由的背后,还要有寻求自由的激情,或者说使命感。这大约是我最近一年的一个思想转变,追求自由,但非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难有使命感。
阿木喜欢这个思路。体谅现实的艰难,因为学生和老师都生活在现实里面,但是人不能以现实来限制自己的脚步。胡适后来离开大陆去台湾留下一句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你要使得这个世界更自由,你就要容忍别人的不自由,包括你自己的不完美,否则这个世界不能变得更自由。第一,你不要想着去改变一切,第二个呢,你首先按照你的基本价值观念,改变你自己。然后你要为你的价值的实现,采取相应的行动,并承担风险。朱自清写过一篇文章,说“教育是一种信仰”。相当一部分人都是以技术来赢利教育的成功,“我能理解他们这样干,但我不会那样做”。第一个充分地阅读,第二个是生命的体验。阅读本身是体验,他在做《理想国》精读课程的时候,把自己向学生开放,学生有什么想说的,就随时过来聊聊。

“瓯江书院”, 具有课程的图书馆
“瓯江书院,我的理解是具有课程的图书馆。”阿木如斯说,“接近传统命名,走得更远。它是非一般意义上的图书馆,最大的特点与日常教学有关,具有课程功能,有相当的独立性。”
书院可以有独立课程,也会与其他场馆及社会机构展开课程合作。尝试自己做课程,比如他现在正在做的《理想国》的校本课程,也支持其他老师做课程,包括手工之类的。
课程类型:可以有1-2节课内完成的微型课程,就像一次小活动或小讲座,如手工课程、共同分享某篇文章等;可以有3-4节课内完成的小型课程,如共读龙应台《目送》;可以有5-10节课完成的中型课程,在一学期内完成;可以有10节课以上的大型课程,一学年或三学年完成;可以有非连续性的,以讲座形式展开的课程,比如公民课程;可以有假期专题课程,如暑期逻辑训练营、名著精读、综合课程(如游学)等,这些自选课程可考虑收费;当然也可以有课程定制,不过这是以后的事了。这里可根据学校实际开发诸多特色课程、学生课程等。
装修的方案我们都已经初步设计好了。蓝图中选中了温州翔宇中学中的三块:一个翔宇贝壳馆楼下的现在的图书馆(后门拓展庭院读书廊)、南门靠河地方地块、体育馆附近。
第一块基本的物理空间,比如阅读区,专题区偏重思想藏书,相当于给老师开辟了一个空间,还典藏区、小说区,还有“以声”馆——以声传情,以声达意。还有“产品”:报刊、杂志、读本、公众号等,既具备对内也对外的功能。
行走在阅读的“理想国”里,“在这几年中,我慢慢开始了一个系列的梦想,编写一套“思享者”读本,完成一个中学哲学课程,参与建设一座图书馆,规划一系列的图书馆讲座和读书沙龙,甚至在离开人世前办一所有意思的学堂。”阿木说:“人的一生其实只有一件事——寻找自己。为此我们出生、成长、求学、工作、娶妻或嫁人、生子、衰老、死亡,我们也向后寻找传统,向周围寻找亲人,寻找同道,寻找集体,向前寻找希望,寻找家园,并且向上寻找信仰。从哪里开始呢?我想,还是从今天。”

(本文经过叶玉林老师本人审核与修改)

